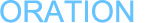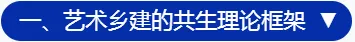11月28日,由中国美术学院指导,中国美术学院城乡统筹综合研究院、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主办,中国美术学院望境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天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新时代乡村共同体白马湖论坛成功举办。论坛以“深化组团式发展,构建乡村共同体”为主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乡创教席主持人向勇发表《组团式发展的艺术乡建机制与模式:一个共生理论的视角》主旨演讲。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
<!--S 全屏播放 full_screen_mv-->
重播 分享 <!--点赞后 加className selected--> 赞 <!-- 随便看看 -->
<!-- 有拓展内容 -->
<!-- 广告内容 -->
<!---->
<input data-v-1d1caec3="" type="checkbox" title="显示工具栏" class="aria_hidden_abs" aria-hidden="true" /><div data-v-1d1caec3="" class="js_control video_opr video_opr_normal padding_play_bar">
<video data-v-1d1caec3="" src="https://mpvideo.qpic.cn/0b2edeaacaaan4aer2tfdntvagodaemqaaia.f10002.mp4?dis_k=0d6592925415e346860ec5502eff51e4&dis_t=1734920263&play_scene=10110&auth_info=bM7/vd0lVJTO9J9+PojdgMlSCDpvPR1kNGASbjBAfUBddCJHUBNqcjhICTZJdQQhZDgFG3s3&auth_key=0edd0bf4d9ea841018b8bf1834c801e7&vid=wxv_3776533197509230598&format_id=10002&support_redirect=1&mmversion=7.0.20.1781" poster="http://mmbiz.qpic.cn/sz_mmbiz_jpg/fVoDmFJeP1ticR9f2HuCs6j4LoCiauJhcvlf8iaJfog2dhnblV8Ugia4JPknhqcD7QNudOXib2EfKx1UCcN0H52MtGQ/0?wx_fmt=jpeg&wxfrom=16" webkit-playsinline="isiPhoneShowPlaysinline" playsinline="isiPhoneShowPlaysinline" preload="metadata" crossorigin="anonymous" controlslist="nodownload" class="video_fill"> 您的浏览器不支持 video 标签 </video></div>
继续观看
新时代乡村共同体||向勇:组团式发展的艺术乡建机制与模式——一个共生理论的视角
,
新时代乡村共同体||向勇:组团式发展的艺术乡建机制与模式——一个共生理论的视角
<audio loop="loop" preload="auto"><source src="https://res.wx.qq.com/voice/getvoice?mediaid=MzA3MzA0MTAyNF8xMDAwMDI3Njk="></audio><!---->
<!--E 视频播放器--> <!-- S 视频社交-->
乡村的共生机制并非短期能够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因此在乡村很难在一开始就谈纯粹的经济效益、商业利益,它需要寻求公益与商业、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平衡。这是一种长期主义的乡村营造,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之间起到最优的调试作用,是长期的共生关系的培育。
它一定不是由单一的市场主体、建设主体去考虑个体的价值,而是多元的价值共享。比如我们现在做成一个结构,有乡村的合伙人结构,有乡村新业态的主理人结构,也有每一个村民、共富者的结构,还有外围自上而下的政府主体、社会机构、企业、公共组织等等。
我们参与艺术乡建秉承了链接、赋能、共生这三个关键词。组团式发展的链接最为重要的就是文化的链接。文化的链接包括不同的维度:传统的历史文化、乡村的文化基因;正在流动涌现,在日常生活中生生不息的文化;以及面向未来的,连接外部世界的创新型的文化。通过文化链接,既要对在地的历史文化资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活化,也要对乡土的人文生活进行重建。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相互关联、相互理解和相互交融的关系。以创意设计、美术、音乐、手工艺等为手段,以创新的手段为乡村传统文化元素进行重更新演绎,在空间、生活和业态各方面培育艺术审美品质。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短期和长期实现最优的一种价值分配机制。不同乡建主体通过相互协作、资源共享等方式,共同创造出价值,共同分配这些价值成果。组团式的发展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共生型的乡村。第一个就是自然生态的共生,是指生物间相互依存关系,如种群间的寄生、偏利共生、互利共生,体现生物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共生型社会的生态环境中,各种生物之间紧密相连;第二个就是社会生态的共生。共生理论被广泛用于分析组织、群体间互动,关注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及共生环境三要素,解释不同主体间的协同与影响。在共生型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体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当我们把艺术乡建、组团式的发展和整村运营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推动的一种共生型的艺术乡建的模式。艺术乡建是依托地方的文化资源,将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方式,实现艺术与乡村生活、生产和生态的互动、协作和整合。组团式的发展从空间组团到业态组团到文化组团,它的发展一定是多个村庄跨地域、跨空间进行整体的运营,是全链条、全过程的整村运营。如何整合艺术创意团队,这些团队可能包括输入型的新村民、外来艺术家,以及本地的协同型和培育型艺术人才。由于单一艺术家难以独自推动整个项目,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全面的运营平台机制,以统合人才、技术和资源。艺术介入仅仅是启动和点燃,真正的价值提升需要通过创意和整个产业的赋能来实现,从而实现后续乡村整体产业价值的提升。第一是守乡人、原乡人。怎么能够让他们增强对这个地方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提升对第三方艺术乡建团队的接纳力、包容性和互动性。通过文化链接和乡建团队的文化陪伴,不断提升他们对于在地文化的感知力,以及身上和日常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活仪式、文化节气等等。
第二是新乡人。人才入乡和青年入乡,他们为乡村带来了新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以及资源统合和产业运营的技能。这些新乡人重要的特征在于他们对乡土和村民的深厚情感,他们并非以自上而下的姿态来送温暖或帮扶,而是秉持着与原乡人共同发展、共同提升和共同互助的心态。
第三是归乡人。他们曾经离开地方,如今因各种原因回归,带着对乡村的深厚情感,致力于在原有产业基础上进行提升和创新。
第四是旅乡人,是短暂参与乡村生活的人群。尤其是我们在大学会把很多在学校开设的工作坊、研学营、研学活动跟一些地方结合,让他们以服务型学习的方式扮演一个在地乡民的角色。
所以我们怎么通过重新定义优化村民的角色?在新技术赋能的基础上,农民的角色确实发生变化,不再仅仅由居住地、出生地所赋予,而是在乡村旅居、工作、生活的一种身份,是一种主动选择性的结果。村民的收益也是一个持续的物质回报,更多的可能还是精神回报。自从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已经没有了,老百姓更多的是要追求一种认同感、尊重感、获得感,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均等化的、平等性的参与感的生活状态。政府的角色是通过制定政策、调配资源监管艺术乡建,确保环境设施的支持。特别是在区县一级政府层面,它们需与上级省市及下级乡镇政府协同合作,共同确定艺术乡建方案,统合跨部门资源,形成不同的组团式发展主体、特色、品牌和产业之间的协同。除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还要有第三方社会组织。这里面包括很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团组织,这样的乡建主体串联上下之间的基层自发和上面强势资源导入的平衡,建立起基于乡村资源连接,我们把它叫做弱连接和强连接相统合成一种巧连接的模式。
不管是商业企业还是其他企业,都应秉持社会企业的思路、定位。企业不止是承担社会责任参与乡村建设,更重要是把乡村事业作为企业经营的一种使命。包括科技企业、文创企业,也涵盖农业企业。艺术乡建在文创基础上去统合科创、农创,把一二三产紧密整合。科技企业推进科技助力乡村发展,结合乡村的在地资源,促进乡村经济繁荣;文创企业创新转化乡村文化,制造市场化的文化产品,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农业企业运用现代农业技术,提升农业附加值,打造特色农业景观,实现艺术乡建与农业的融合。

< 自然生态环境
艺术乡建的生态资源:充分利用乡村山水,保护自然资源,遵循生态原则进行艺术创作和乡村建设,防止过度开发,实现艺术与自然和谐共生。
艺术乡建的生态建设:乡村的优美环境为艺术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同时也吸引游客体验,推动乡村旅游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艺术乡建的生态保育:在发展艺术乡建过程中,需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确保艺术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
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个资产,也是一种乡村进行组团式发展非常重要的公共吸引物和共享型舒适物。所以生态资源保护、生态资源建设和生态资源的保育本身就是我们提取乡村发展自然有机、可循环有序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种生态来源。
政府引导:乡村振兴政策鼓励艺术乡建,税收优惠吸引企业投资,土地政策保障创作空间和设施建设。人才扶持:政策支持艺术团队和企业在乡村开展业务,增强艺术乡建的活力和创新性。资金支持:直接影响艺术乡建的积极性和共生模式的有效性,决定项目的可持续性。技术助力:确保艺术创作和旅游设施用地,为艺术乡建的长期发展提供稳定基础。社会风俗:乡村风俗对艺术建设有深远影响,和谐邻里促进艺术家与村民合作。
传统价值观:乡村传统价值观提供创作素材,通过节日、民俗活动展示艺术与文化。
价值认知:对外乡文化的尊重度影响艺术乡建影响力,良好环境促进各单元互动融合。为了统合传统农耕时代固态型、流动性差的乡村,以及后来出现的空心化现象,弥补和改善乡村创意的生态,需要通过社会文化环境、社会风俗、传统价值观的转化,凝练乡村的价值认知,来真正的构建基于乡村共同体的组团式发展。
所以说既有互利共生的机制:乡村文化传承创新,艺术家借鉴乡村文化,创作现代艺术,村民学习艺术技能,提升审美,共同推动乡村文化创新;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旅游企业与农业企业合作,游客体验农事活动,品尝特色农产品,双方提升知名度和销售,带动乡村产业协同发展。
也有扩散共生机制:既有空间区域的扩散,知名艺术家入驻乡村,个人魅力吸引外界关注,提升乡村知名度,为后续发展创造条件;也有产业价值的扩散,政府加大投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优化运营效率,促进整体发展环境优化。< 地方认同的构建
乡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需求,是艺术乡建的内在驱动力,艺术家与村民因文化共鸣形成共生。它的公益性较强,浸入性、深度性对于乡建者来说要求较高,一定是跟村民的一种陪伴,如何维持、提炼和发现乡村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的需求。
乡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催生新的发展模式,艺术乡建带来的产业机会促使各单元基于经济利益合作,形成共生关系。它是一个根本,是一个连接。艺术、土地、政策、资金多方面资源互相结合,形成多元运营模式,旅游收入循环用于艺术与乡村建设。
共生关系促进知识交流和技术创新,艺术理念、管理经验、乡土智慧汇聚,推动模式创新,如新型旅游产品、数字化艺术乡建。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